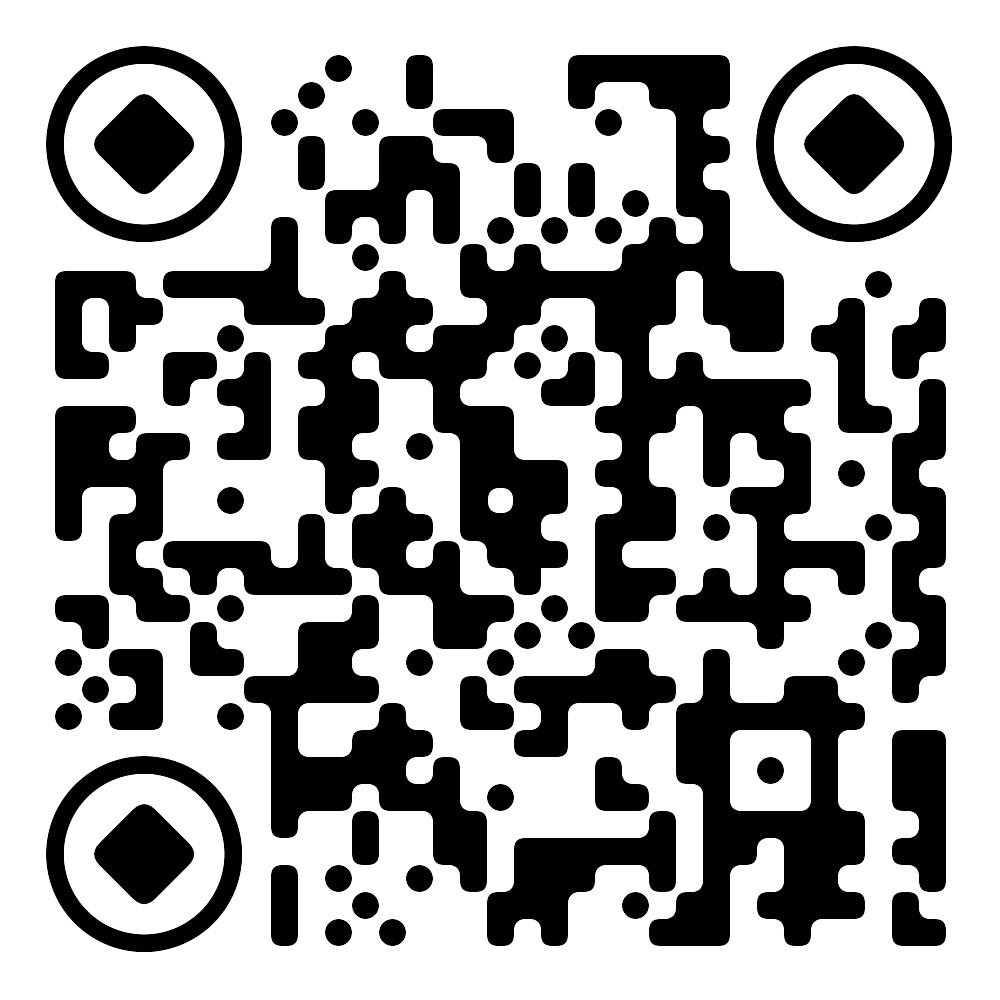风从窗缝里钻进来,带着些许凉意,桌上热气袅袅的水汽,把窗外的景象晕染得模糊不清。临近中秋节,空气里好像都飘着月饼的甜香,只是这香气里,总少了点家的味道。
指尖摩挲着温热的茶杯,思绪忽然飘回上次回家。父亲鬓角的霜又厚了些,原来能轻松扛起半袋大米的肩膀,如今拎桶水都要歇一歇;母亲的眼睛也不如从前清亮,穿针时总要把线头凑到鼻尖,眉头皱成个小小的疙瘩。那些曾以为永远挺拔的身影,竟在不知不觉中增添了岁月的痕迹。
“莹儿,来帮爸爸剥蒜。”每次我在家时,父亲总早早就扎进厨房忙活,案板上码着刚买的新鲜食材。他系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围裙,切肉的动作依旧麻利,我便搬个小板凳坐在旁边,手里攥着蒜瓣费力地剥着蒜皮。厨房里的油烟混着肉香飘出来,母亲在一旁择菜,时不时递过几根洗净的葱,一家三口的笑声,把小小的厨房填得满满当当,连空气都浸着暖意。
前两天拨通电话,母亲举着手机在厨房里转,把镜头对着案板上我最爱的核桃馅月饼:“你爸非说要自己烤,面和硬了,皮有点厚。”说完便把手机转向父亲,他正蹲在地上摆弄烤箱,听见这话头也不抬,只嘟囔着,“自己烤得干净,闺女爱吃。”我看着屏幕里他们忙碌的身影,眼眶突然有些微红,仿佛已经闻到了那带着点焦糊味的月饼香,和记忆里的温暖一模一样。
桌上的时钟慢慢走着,每一声“嘀嗒”都像在丈量离家的距离。去年中秋,母亲打了三次电话,第一次问我吃没吃月饼,第二次说阳台的花又开了,第三次却久久沉默,过了好一会儿才轻声说:“你爸在阳台转悠了好久,说想看看你那边的月亮圆不圆。”那时才懂,原来牵挂不是单向的,我在惦记家的同时,家里的灯火也始终为我亮着。
起身走到操场,月亮终于从云里钻了出来,比刚才亮了许多。记得小时候,我总缠着父亲问,“中秋节的月亮为什么是圆的?”他笑着说,“因为中秋了,一家人要团圆,月亮也想凑个热闹。”那时似懂非懂,直到长大后离开家,看着天上的月亮,才突然明白,所谓团圆,从不是月亮有多圆,而是身边有没有家人的陪伴。路边的树影摇晃,这几年早已习惯独自面对风雨,可中秋的思念总如潮水般涌来。就像父亲说的:“一家人的心,再远也紧紧相连。”
风又吹过脸庞,恍惚间仿佛闻到了家里的饭菜香,听见了父亲切菜的“笃笃”声、母亲择菜时偶尔的轻咳声。这些熟悉的声响与香气,不仅照亮了这个夜晚,更照亮了我心里那个永远属于家的角落。原来家从来不是一个地方,而是无论走多远,一想起就会觉得温暖的港湾,是亲人藏在细节里的牵挂,是跨越千里也拆不散的惦念。(陶莹)